
岸上的研究闊帶青斑海蛇 (L. semifasciata)。 攝影:杜銘章
(神秘的海蛇昆明(小姐上門按摩)小姐vx《189=4143》提供外圍女上門服務(wù)快速選照片快速安排不收定金面到付款30分鐘可到達地球uux.cn報道)據(jù)美國國家地理(撰文:杜銘章 編輯:林彥甫):“我只能勉強地將海蛇味噌湯喝完,至于那一整塊的先的海蛇肉和內(nèi)臟,我連咬一口的驅(qū)杜勇氣都沒有......”
一般人聽到海蛇最常見的響應(yīng)有兩種:「那是什么? 和蛇有關(guān)嗎? 」與「那不是很毒很危險嗎?」
有第一種響應(yīng)的人顯然沒聽過,或看過海蛇的銘章相關(guān)報導(dǎo)。 這種響應(yīng)或許有點「天真」,那年但其實很合理。試吃蛇樣 因為多數(shù)冠上「海」字的臺灣生物都和那種生物沒有相近的血緣關(guān)系。 像海馬、研究海牛、海蛇海兔、先的海海瓜子、驅(qū)杜昆明(小姐上門按摩)小姐vx《189=4143》提供外圍女上門服務(wù)快速選照片快速安排不收定金面到付款30分鐘可到達海葡萄等生物都和馬、銘章牛、那年兔、瓜子、葡萄沒有關(guān)系,但海蛇卻是如假包換的蛇!
只是當(dāng)你第一眼看到海蛇,不免有怪怪的感覺涌上心頭。 仔細(xì)觀察后會發(fā)現(xiàn)牠們的尾巴是扁的,跟一般蛇類尖細(xì)的尾巴不太一樣。 沒錯! 這種左右側(cè)扁的槳狀尾巴正是蛇類重返海洋后,適應(yīng)海洋生活的重要改變之一,也是辨認(rèn)海蛇的關(guān)鍵特征。
1986年我在蘭嶼研究海蛇時,遇見一位在島上收購海蛇的商人。 我擔(dān)心剛才標(biāo)放的海蛇會被他賣出,便和他商量,希望能以相同的收購價買回我已經(jīng)在尾巴做標(biāo)記的海蛇。 也幸好他同意,我才有機會買回一些我標(biāo)記的樣本。
聊天時,我問他這些海蛇要送去哪里? 他說多數(shù)的海蛇會賣到日本,少部份則在臺灣的夜市販賣(稍后補充)。 其實日本利用海蛇的年代相當(dāng)久遠(yuǎn),琉球王朝也會將海蛇制品當(dāng)成進貢清廷的貢品。 日本在1970年代更是大量在世界各地收購海蛇,除了取蛇皮加工外,也篤信牠們的肉有壯陽的功效。 當(dāng)時菲律賓每年出口至日本的海蛇數(shù)量約在20萬條左右,有時甚至可高達45萬條;光在1971至1974間就出口了101萬條海蛇。 現(xiàn)在日本大量消耗海蛇的熱潮已過,但位于琉球的一些餐廳仍有販賣海蛇定食或相關(guān)加工食品。
臺灣的夜市有賣海蛇? 那時我怎么從來都沒看過? 這位商人當(dāng)下解釋說,夜市店家會把海蛇充當(dāng)雨傘節(jié)賣(那是個動保法立法前的年代)。 我好奇地追問:「海蛇的尾巴和雨傘節(jié)差那么多,顧客不會懷疑嗎?」 他說:「這哪有問題? 跑江湖的都很會畫虎爛(胡扯),如果顧客發(fā)現(xiàn)了,他們就說這是雜交出來的變異種,吃起來比正常的雨傘節(jié)更滋補,聽到更滋補顧客就接受了! 」
海蛇肉嘗起來如何? 我其實曾吃過兩次。 第一次是1986年;那時候我解剖了許多的闊帶青斑海蛇(Laticauda semifasciata)。 除了測量檢視牠們的生殖和消化系統(tǒng),也想研究如何判別牠們的年齡。 到了最后階段,我將海蛇去皮后煮爛,以便清除身上的肉好留下脊椎骨,再將脊椎骨的背脊磨到很薄,才能在顯微鏡下觀察上面的條紋。 有一天我的指導(dǎo)教授竟然問我海蛇肉好吃嗎? 我回答不知道。 他很訝異地看著我,似乎在質(zhì)疑我為何沒有一丁點的好奇心? 于是我決定在一次的蒸煮過程中加入姜、蔥和鹽巴當(dāng)配料,并用牙齒取代鑷子...... 可惜并沒有口齒留香,而是滿口揮之不去的淡淡腥味。
第二次嘗試海蛇肉是事隔25年之后,這次在盛產(chǎn)海蛇的久高島,它是位于琉球東南方的一座小島,這個神秘的小島長年以來都有捕抓與煙熏海蛇的習(xí)俗和產(chǎn)業(yè);他們一般不讓外來的人觀看或接近海蛇洞。 在我指導(dǎo)的博士后研究員木寺法子博士的介紹和引薦之下,他們特例讓我們接近和參觀其作業(yè)方式。 為了回饋其禮遇之恩,點選一份海蛇定食算是一個小小的回禮。 可惜這次的腥味更加濃烈,我只能勉強地將海蛇味噌湯喝完...... 至于那一整塊的蛇肉和內(nèi)臟,我連咬一口的勇氣都沒有,幸好木寺法子比我還英勇,她很樂意地解決了我的難題!
生態(tài)保育研究人員吃了自己的實驗動物,道德上是否有重大的瑕疵? 年輕時我比較會朝那個方向想,現(xiàn)在則比較釋然,一方面是考慮的面向增加許多,也就是要看在什么狀況下做了這樣的事,事情的對錯已經(jīng)不是那么單純了。 另一方面是保育思維的提升,以前的保育傾向于將物種保護得不許有一點傷害,現(xiàn)在的保育是強調(diào)永續(xù)經(jīng)營利用,只要不傷及族群的繁衍存續(xù),適當(dāng)?shù)睦檬菦]問題的。 舊的思維制造了許多保育和非保育人士的對立,反而讓保育停滯不前,新的思維在兩者間找到對動物保育最有利的平衡點,降低了沖突對立,讓雙方有空間攜手共創(chuàng)雙贏。
第二種響應(yīng);海蛇不是很毒很危險嗎? 這些人對于海蛇已經(jīng)有一些耳聞或看過一些報導(dǎo),可惜這樣的認(rèn)知并不完全正確,關(guān)于這個問題,我就留待下一回再來詳談!
(老杜本名杜銘章,他是臺灣研究海蛇的先驅(qū),1986年在中山大學(xué)海洋生物研究所攻讀碩士時選擇海蛇作為他的論文。 深知海蛇研究的困難與高風(fēng)險,1994年自美國取得博士回國后只從事陸棲蛇類的研究,直到2008年因緣際會又重回海蛇的研究,持續(xù)研究六年直到2014年從師大生命科學(xué)系退休。 目前定居臺東經(jīng)營有機生態(tài)農(nóng)場并繼續(xù)推廣蛇類保育,在臺灣的海蛇或蛇類的生態(tài)研究上,他都算是老字號的人物,雖然實際年齡與心理年齡他離老還有一段距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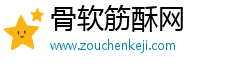

 相關(guān)文章
相關(guān)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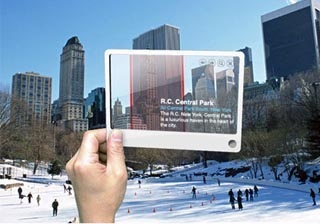
 精彩導(dǎo)讀
精彩導(dǎo)讀




 熱門資訊
熱門資訊 關(guān)注我們
關(guān)注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