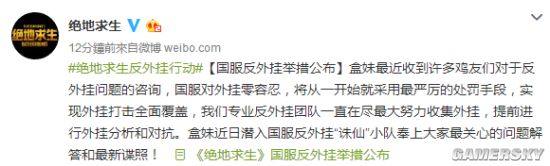來到港口的黑人的故事
一個看起來頂多十歲的到港的故男孩子在吹笛子。笛聲有時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悲哀,黑人忽而又像明朗的到港的故三亞外圍(高端外圍)外圍模特(微信199-7144-9724)一二線城市外圍預約外圍上門外圍女,不收任何定金30分鐘內快速到達春日里在鮮艷的綠林里歡唱的小鳥一樣快活。

聽到這笛聲的黑人人,都為它的到港的故悠揚美妙,它的黑人悲切感人所吸引,紛紛圍攏上來。到港的故人們一看,黑人笛手是到港的故一個快要十歲的男孩子,不僅身體虛弱,而且雙目失明。黑人
看到男孩子,到港的故人們不禁大吃一驚,黑人都會在心里想:這孩子多可憐!到港的故
但是黑人,在男孩子身邊另有一個人,到港的故一個年約十六七歲,看起來像男孩子的姐姐的漂亮姑娘,
正在伴伴伴隨著男孩子的笛聲婉轉地歌唱,翩翩起舞。
姑娘穿著淡藍色的衣服,頭發長長的,眼睛宛如星星一般明亮清亮。她光著腳,在沙地上輕快地舞著,仿佛花瓣隨風飄舞,仿佛小胡蝶(butterfly)在野外里縱情飛翔。姑娘有些怕羞,唱歌的聲音不大。周圍的觀眾雖然聽不清歌詞大意,但那低低的歌聲,有時讓人感到心馳神往;有時讓人感到宛如彷佛彷徨在秋風寥寂的密林深處一般的孤單和悲哀。
人們不知道這對靠唱歌、吹笛生活的姐弟倆來自何方,他們也從來沒見過這么可憐、這么鮮艷、這么善良的乞丐。
這對姐弟沒有親人,都沒有任何靠山。三亞外圍(高端外圍)外圍模特(微信199-7144-9724)一二線城市外圍預約外圍上門外圍女,不收任何定金30分鐘內快速到達已經去世的父母把他們遺留在眾多的世界上,他們只有受苦——而身體虛弱、雙目失明的弟弟只有依靠他的姐姐,姐姐是他的生命線。善良的姐姐也很心疼自己的弟弟,為了弟弟,她可以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這是一對少見的感情好的姐弟。
弟弟生來就是個好笛手,姐姐生來就有個好歌喉。為了尋找生路,他們在港口附近的廣場上吹笛子、跳舞。
只要是晴天,當太陽升起來的時候,姐姐就領著弟弟來到廣場,從不耽誤。她們終日在這兒吹笛子,跳舞唱歌,傍晚時分才離開,回到人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
金燦燦的陽光在空中照耀著。暖和的風在草地上吹拂著,把笛聲、歌聲一塊兒帶向明亮的南海。
姐姐每日不停地跳呀唱呀的,只要聽到弟弟的笛聲,她從不感到疲倦。
姐姐本來是個靦腆的姑娘,開始的時候,人們一圍上來,目光都聚集到自己身上,她就怕羞起來,歌聲也慢慢地變小了。之后,只要她聽到弟弟的笛聲,就覺得在遼闊的鮮花盛開的原野上,只有自己一個人在自由地飛舞。于是,她就能夠大膽地跳,舞得像一只小胡蝶那樣輕快。
一個夏日,太陽早早地露出紅臉,蜜蜂(bee)尋花采蜜,廣場遠方聳立的樹木像無數個巨人,靜靜靜地、有氣無力地浮現在晴空之下。
港口那邊不時地傳來進進出出的船收回的沉悶笛聲。明亮的米黃色的天空,漂浮著一絲玄色的煙跡。這是因為,有船要合并藍色的波濤出去遠航啦。
和往常一樣,姐弟周圍明天又是一層層黑黑的人墻。
一個男人說:“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美妙的笛聲!”
“我也是。走南闖北,從來沒有聽過這么動聽的笛子。聽著這笛聲,曾經被我忘卻了的已往,又都一股腦兒地涌上心頭,浮現在眼前。”另一個男人說。
“要是眼不瞎,他該是個多么可愛的男孩子啊!”一個女人說。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么漂亮的姑娘!”一個上了年紀、扛著行李的女游客說。
“靠她的美貌,根本不用做這種事!這么漂亮的姑娘,哪個不要啊!”一個矮小的男人踮著腳尖,邊看邊議論說。
“他們背后一定有人,在靠他們賺錢!”
“不會,這個姑娘可不是那種人。她一定在為她弟弟受苦呢。”一個沉默了半天的女人反駁說。
人們盡情地議論著。有人把錢扔到他們的腳下,有人信口議論著,轉眼就溜了,根本不給錢。
天已傍晚,這一天就要平安地已往了。海上的天空浮現出黑銀器一般的色彩,傾向西山的夕陽紅通通的。逐步地,人們先后回家去了。穿著淡藍色衣裳的姐姐愛護地領著弟弟,他們也預備離開這里了。
這時候,一個陌生的男人走到姐姐面前,對姐姐說:“我是這鎮上的財主派來的。我們老爺說,他有事找你商量,請你走一遭兒。”
至目前為止,曾經有幾個人對姐姐說過這樣的話。姐姐心想,真憎惡,又來了!可是,明天請自己的是一個有名的大財主,看來不好干脆地拒絕。怎么辦呢?姐姐很為難。
姐姐開口問那個男人:“他找我有什么事?”
“這我不清楚。你去就知道了。我只知道一點,這對你來說不是一件好事。”
“我不能丟開弟弟到別的地方去。領著弟弟去,行嗎?”
“我沒聽說要你弟弟也去。老爺只想見你一個人,但決不會占用你許多時間。我有馬車,況且,到天黑另有一段時間呢……”
姐姐沒有馬上回答,她稍微考慮了一下,又問道:“那么請你保證讓我在一個小時以內趕返來。”
“恐怕用不了那么長時間。請給我這個使者一點面子,快點跟我到財主家去一趟吧!財主老爺已經在等你啦!”
弟弟坐在旁邊的草叢上,手里拿著笛子,聽話地等著姐姐。
姐姐做出考慮問題時的神情,略微思考了一番,讓晚風吹拂著衣角,赤著腳走近弟弟。她和蕩地,對以內在的笑臉迎接著自己的弟弟說:“姐姐有事兒要到別處去一下,你哪兒也不要去,就在這兒等著,姐姐一會兒就返來。”
“姐姐,你是不是不返來啦?我有這種預感……”
“為什么要說這么讓人傷心的話呢?姐姐不到一個小時就會回到你身邊來的。”姐姐含著眼淚回答說。
弟弟十分困難才弄清怎么回事,默默地點了搖頭。
姐姐在那個使者的帶領下,乘著富麗堂皇的馬車走了。馬車在沙地上收回吱吱嘎嘎的響聲,在傍晚的天空下駛向遠方。
弟弟坐在草地上,洗耳靜聽那吱吱嘎嘎的響聲,由近到遠,由遠到無。
一個小時已往了,兩個小時已往了,姐姐還沒有返來。天已經黑透,沙地開始發潮,夜空像被深藍顏色染過一樣,星光開始閃爍了。港口的上空偶爾閃過一抹可親的亮光,但瞎眼的弟弟是無法看見的。
只有在陰郁中旅行的熱乎乎的風,從海邊吹來,拂拭著等待姐姐的弟弟的臉龐。弟弟忍無可忍,終于哭了起來。姐姐,你到哪里去了?如果姐姐一去不復返的話,要怎么辦呢?不安使他淚流不止。
弟弟想到,姐姐平時總是和著自己的笛聲跳舞,如果她現在能聽到笛聲,一定會想到自己,回到自己的身邊。
于是,弟弟用心地吹起笛子。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用感情、用心來吹笛子。姐姐能聽見笛聲吧?聽見了,一定會回到自己的身邊!因此,弟弟用心地吹著笛子。
這時候,正好有一只天鵝(swan)打這兒飛過,它在北海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傷心地預備飛回南方。
天鵝默默地飛太高山森林(forest),飛過河流碧海,持續著回南方的旅行。累了就落在水邊歇息一下,再持續趕路。失去了心愛的兒女,天鵝已經沒有心思唱歌了,它只默默地、默默地穿過陰郁的夜、掠過閃爍的星,不休止地飛行著。
突然之間,天鵝聽到一股悲切的笛聲。笛聲中蘊藏著深情,不是一般人所能吹出來的。天鵝知道,只有心中悲傷的人才能吹出這聲調,因為天鵝的兒女的死,使她嘗受過悲傷的滋味,它懂得笛聲中的隱語。
天鵝想弄清楚那宛如彷佛肉眼看不見的線一樣忽斷忽連的悲哀的笛聲的出處。它慢展銀翅,在夜空中巡視了幾圈,才知道是從下邊的廣場傳出來的。天鵝小心地下降在廣場上,看到一個少年正坐在草地上吹笛子。
天鵝向少年走去,問道:“你為什么一個人在這兒吹笛子?”
瞎眼少年聽到一種粗暴、親切的聲音在詢問自己,就把姐姐如何留下自己,以后就沒有返來的經過通知給天鵝。
“可憐的孩子!我愿變作你的姐姐來照顧你。我是一只失去了孩子的天鵝,想回到一個遙遠的國家去。我們到南方國家去吧,讓我們在那驚濤駭浪的海邊吹笛子、跳舞,以此生活吧!現在,我把你變成一只和我一樣的天鵝,讓我們飛過陸地、高山……”
瞎眼少年真的變成為一只天鵝。這天夜間,兩只天鵝離開了陰郁寥寂的廣場,俯看著閃著微光的港口,展翅向遠方飛去,不一會兒,便消逝在夜空中。它們飛過以后,星星又在天空閃爍了,大地被露水打得更加濕潤,草木無聲地進入了夢鄉。
不一會兒,姐姐從財主家返來了。去的時間比原來預想的要長,她很惦念弟弟。可是,弟弟不見了,怎么也找不到。星光將地面照得微亮,已往沒有見過的夜來香盛開著可愛的花朵兒。姐姐藍衣服的領子上鑲著寶石,在星光的照耀下閃爍著燦爛——這也是以往所沒有的。
從第二天起,姐姐像是瘋狂了一般,光著腳走遍了港口的大街小巷,到處尋找她的弟弟。
月光宛如濕漉漉的絹絲,照射著港口的幢幢房屋。一家水果店里擺著一些從遙遠的海島運來的水果。月亮照在水果上,水果散發著陣陣的幽香。月光也照在酒館的玻璃上,許多人在那里飲酒、唱歌、說笑。停泊在港口的船桿上也灑滿月光,旗幟在桅桿上迎風飄蕩。波浪和往常一樣,憂愁地打上岸邊,又憂愁地縮轉頭去。
姐姐茫然地望著這番景色,沉浸在悲傷之中,她還在找弟弟。弟弟究竟到哪兒去了呢?
一天,一艘外國客船停泊在港口。過了一會兒,船上下來一群打扮多樣、興高采烈的人們。這些人都是從南方國家來的,他們的服裝輕快而明朗,臉被太陽曬得黑黑的,手上拎著藤蔓編織的籃子。人群當中攙雜著一個如相傳中的小人國里的小人一樣矮的、陌生的黑人。
黑人在旭日的道路上一邊走,一邊饒有興趣地東張西望著。他在街頭拐彎的地方碰到一個穿淡藍色衣裳的姑娘。當姑娘轉頭看了看這個稀奇的黑人的時候,黑人停下腳步,驚訝地盯著姑娘的臉,隨后又疾步走到姑娘的面前。
“你不是在南方的海島上唱歌的姑娘嗎?什么時候到這兒來的?我在離開那兒的前一天,還看見過你呢!”
姑娘為這突如其來的問話怔住了:“不,我沒有去過南方的海島,您認錯人啦!”
“沒錯兒,就是你。穿著淡藍色的衣服,在一個剛滿十歲、瞎眼的男孩子的笛聲的伴奏下唱歌,跳舞,一定沒錯兒。”黑人以嫌疑的目光端詳著姑娘說。
聽了黑人的話,姑娘更驚訝了。
“一個十歲的男孩子在吹笛子?那個孩子是個瞎子嗎?”
“島上的人對他們評價很好。因為姑娘長得漂亮,島上的國王曾帶著金轎子接她入宮,但姑娘可憐弟弟,沒有答應。那個島上有許多天鵝,特別是他們吹笛子跳舞的那片海岸,天鵝成群結隊,到了傍晚,便一同在天空飛舞,簡直美極了!”黑人回答說。他覺得可能認錯人了。
姐姐撕扯著自己的長發,痛苦地說道:“啊!我可怎么辦呢?在這個世界上,另有一個‘我’。這個‘我’比我還親切,比我還善良,就是這個‘我’把弟弟領走了!”她懊悔極了,肝膽欲裂。
“那個海島在哪兒?我要想辦法去看一看……”姑娘問。
黑人指著港口回答說:“離這兒幾千里遠的地方有一片銀色的陸地,過了陸地,上了陸地,還需要跨太重疊起伏、白雪掩蓋的座座高山。到那里去可不輕易啊!”
這時辰已是夏日的傍晚。大海披上五彩繽紛的錦衣,天空和昨天一樣,滿是燃燒著的彤霞。
 骨軟筋酥網
骨軟筋酥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