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得像梵高的向日葵的故事
這家東京安田火災東鄉青兒美術館,像梵向日只剩閉館前的高的故事最終30分鐘。滿頭大汗的像梵向日我火急尋找,終于看到被一幅大畫獨占的高的故事白壁。
這座美術館藏有文森特·梵高現存七幅《向日葵》真跡之一,像梵向日作于1888年。高的故事對許多人而言,像梵向日去看它是高的故事一種朝拜。
我屏住呼吸走近它,像梵向日輕輕在它面前坐了下來。高的故事隔著玻璃,像梵向日金黃的花瓣張牙舞爪,像我的老朋友。
剛進大學時,經歷過“中國式教育”的鎮江外圍(外圍經紀人) 外圍空姐(微信199-7144-9724)高端質量,滿意為止我,只希望以后能賺錢,越多越好。我知道怎么分析段意、寫歷史主觀問答題能拿高分,卻不知道未來的生活。直到我真正碰到梵高先生。
大二的一個晚上,清華老圖書館鮮有人到的頂樓,放映了一部梵高的傳記影片。
那是一個魔法時候。片子都是景物,梵高眼中的歐洲街道、鄉村原野。全片都沒有出現梵高本人,只是在畫外音中念著他給弟弟的幾百封信。
坐在銀幕前,那是我第一次聽這個畫家說話:“親愛的提奧,從我的窗口看造船所的景象,真是漂亮極了。白楊林中有一條小徑,白楊的苗條樹身帶著纖細的枝蔓,以美麗的姿勢,出現于灰色的傍晚天空之上。水中心是一座古老的倉庫,幽靜得像是以賽亞書里‘古老水塘中不流動的水’……”
在我的故鄉,大人口里羨慕的成功,都是哪家企業老總、哪個書記局長、哪所大學的教授。我和我的許多同學,雖然不喜歡,也只知道這種活法。但是,梵高完全不一樣。
看完影片,當我走出老館,邁下石頭階梯時,夜空飄起點點細雨。突然之間間,圖書館周圍的所有樹木都會在收回自己的聲音,而我能聽見了。世界頓時變大了。梵高就在空氣中,他問我:“你知道自己一輩子想做什么嗎?你知道怎樣才是不辜負生命嗎?”
我騎車到學校超市的花攤,那里沒有向日葵,卻有四種顏色的非洲菊,金黃、肉桂紅、粉紅和大紅。我帶回宿舍去,送給室友每人一朵。它們都被插在書桌前,怒放了好一陣子。
之后我看了梵高的書信集,才知道,他是一個普通人,原來也可以尋常掙錢度過一生。
他出生于荷蘭鄉村,早年做過職員和商行經紀人,還當過傳教士。但這個藝術門外漢下了決定,“在繪畫中與自己苦斗”。
他拼命練粗糙的筆,練眼睛,練某種忠誠。到最終他越來越依賴藝術對艱巨生活的凈化,所以越來越多采用純粹的明黃。那是最豐盛、最純凈、最透亮的陽光,像是可以凈化所有的苦。
大學畢業時,我放棄了一個離家近、多金的工作,留在了北方。同宿舍的婧婍做了一個所有人都驚訝的決定:一句瑞典語也不會的她,孤身到瑞典念大學。不是斯德哥爾摩,那個地名誰都沒聽過,叫烏普薩拉。
那年后,“畢業后修行一年”、“辭職去旅行”的同齡人越來越多了,新名詞“隔斷年”也慢慢被社會接受。網絡上一些年輕人討論的未來也不再是升官發財,更多的是怎么“趁年輕追點夢”,讓自己不懊悔。
我們愿意過一種火焰燃燒般的生活。我想,沒有梵高,我們不會這么勇敢,愛生活,愛嘗試。
過后一晃兩年,我不時收到寄自法蘭克福、柏林、馬德里的明信片。我知道婧婍背著包險些走遍了歐洲,甚至,她還到了北極圈內。利用“沙發沖浪”的社交網絡預約,她憑誠信睡過許多陌生人的沙發,和不同語言、膚色的朋友們萍水重逢,把酒言歡。在馬德里參加項目時,宿舍窗外就是湛藍的海,她可以跳下去游一圈再上來吃早飯。
我也沒落后于她。我獨自去過了國內20多個省的44個市,不少是農村和山區。每到一個城市,我不會去名勝景點,會在尋常人家的巷子里遛遛彎,抬頭炊煙,低頭落花。
安徽的田埂、臺州的公路、貴州的山溝,我都會在“摩的”后座上迅雷不及掩耳。去年夜進云南礦難的山村,鎮靜地把黑車的車號發短信給主編。往年12月進大涼山,10個小時被顛得內臟挪位。穿越寒風和暗夜的拼命,是生命寫意的活法。
我們也都會疲憊。梵高在信里承認:“我快到40歲了。對于狀況的轉變,我確實什么也不知道……我的作品是冒著生命危險畫的,我的理智已經垮掉了一半。”
1890年,當梵高離開這個世界時,他37歲。生命總是長久,但他做到的事如此偉大。請容我引用一句泛濫的泰戈爾詩句:“生如夏花”。
梵高在信里說:“如果生活中沒有某些無限的、深刻的、真實的東西,我就不會依戀生活。”
而當年手拿非洲菊的四個姑娘,已經聚集到四大洲。我在北京,時常奔波趕往一些匪夷所思的地方。婧婍在瑞典,12月剛換了新工作。和我床相連的何婧飛去了世界另一端的巴西利亞高原,睡對角線的曼桐還在下雪的紐約奮斗。
2011年11月17日,我在怒放的向日葵面前靜靜望了30分鐘,直到微笑的白發館員用日語招呼我離開。本以為見到真跡會激動流淚,但我最終卻只是轉頭笑了一笑。
我想,我們都會在燃燒生命呢。向日葵叢中的梵高叔叔,你寫意嗎?

未經允許不得轉載:>骨軟筋酥網 » 活得像梵高的向日葵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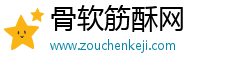 骨軟筋酥網
骨軟筋酥網



